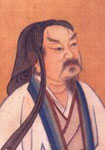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(fēng)于規(guī)林·其一
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(fēng)于規(guī)林·其一朗讀行行循歸路,計日望舊居。
一欣侍溫顏,再喜見友于。
鼓棹路崎曲,指景限西隅。
江山豈不險?歸子念前涂。
凱風(fēng)負(fù)我心,戢楪守窮湖。
高莽眇無界,夏木獨森疏。
誰言客舟遠?近瞻百里余。
延目識南嶺,空嘆將焉如!
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(fēng)于規(guī)林·其一。魏晉。陶淵明。 行行循歸路,計日望舊居。一欣侍溫顏,再喜見友于。鼓棹路崎曲,指景限西隅。江山豈不險?歸子念前涂。凱風(fēng)負(fù)我心,戢楪守窮湖。高莽眇無界,夏木獨森疏。誰言客舟遠?近瞻百里余。延目識南嶺,空嘆將焉如!
譯文
歸途漫漫行不止,計算日頭盼家園。
將奉慈母我欣歡,還喜能見兄弟面。
搖船蕩槳路艱難。眼見夕陽落西山。
江山難道不險峻?游子歸心急似箭。
南風(fēng)違背我心愿,收起船槳困湖邊。
草叢深密望無際,夏木挺拔枝葉繁。
誰說歸舟離家遠?百余里地在眼前。
縱目遠眺識廬山,空嘆無奈行路難!
注釋
計日:算計著日子,即數(shù)著天數(shù),表示急切的心情。舊居:指老家。
一欣:首先感到歡欣的是。溫顏:溫和慈祥的容顏。詩人這里是指母親。侍溫顏:即侍奉母親。
友于:代指兄弟。《尚書·君陳》:“孝乎惟孝,友于兄弟。”
鼓棹(zhào):劃船。棹:搖船的甲具。崎曲:同“崎嶇”,本指地面高低不平的樣子,這里用以比喻處境困難,《史記·燕召公世家):“燕北迫蠻貉,內(nèi)措齊晉,崎嶇強國之間。”
指:顧。景:日光,指太陽。限西隅(yǘ):懸在西邊天際,指太陽即將落山。限:停止。隅:邊遠的地方。
歸子:回家的人,作者自指。念:擔(dān)憂。前涂:前路,指回家的路程。涂同“途”。
凱風(fēng):南風(fēng),《爾雅·釋天》:“南風(fēng)謂之凱風(fēng)。”負(fù)我心:違背我的心愿。
戢(jí):收藏,收斂。枻(yì):短槳。窮:謂偏遠。
高莽:高深茂密的草叢。眇:通“渺”,遼遠。無界:無邊。
獨:特別,此處有挺拔的意思。森疏:繁茂扶疏。
瞻:望。百里余:指離家的距離。
延目:放眼遠望,“南嶺:指廬山。詩人的家在廬山腳下。
將:當(dāng)。焉如:何往。這首詩慨嘆行役之苦,思念美好的田園,因而決心辭卻仕途的艱辛,趁著壯年及時歸隱。
參考資料:
1、孟二冬.陶淵明集譯注及研究.北京:昆侖出版社,2008:100-103
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(fēng)于規(guī)林·其一創(chuàng)作背景
此詩寫于東晉隆安四年(400年),作者陶淵明三十六歲。作者此時在荊州刺史桓玄的幕府中任職。此前,陶淵明奉桓玄之命出使京都建康(今南京市),完成使命后,返途中路過江西,準(zhǔn)備順道回家省親,然而被風(fēng)阻在途中。這首詩就是寫在途中受阻時的情景。
參考資料:
1、孟二冬.陶淵明集譯注及研究.北京:昆侖出版社,2008:100-103
第一首詩總的調(diào)子是抑郁的,但前四句并不沉悶,抑郁中有歡快,淚與笑俱,起伏多變。“行行循歸路,計日望舊居”。歸心似箭,匆忙趕路,心里計算著到家的日子。為了表達歸家的急迫心情,詩人注意了詞語的選擇,“行行”是重言,富有表達力,寫出了詩人奔走不停的祥子;“計日望舊居”的“計”和“望”,準(zhǔn)確而形象地反映出詩人歸家途中的心理活動,詩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別了的“舊居”,去看望自己的親人,他唱道:在行役路上動鄉(xiāng)關(guān)之思,盼與家人團聚,這是人之常情,陶淵明用詩的語言道出了這種人之常情,最容易引起共鳴。
“計日望舊居”的陶淵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。然而,偏偏行船遇風(fēng),被迫在窮湖停船,這當(dāng)然使他苦惱。離家只有百余里,卻回不去,他只好遙望南嶺,對空長嘆,心情是無可奈何的。詩人不僅寫了這種欲歸不得的苦惱,他還借嘆行役的機會表示了對官場的厭倦,對仕途的憂懼,對懷才不遇的抗議。有了這些內(nèi)容,就看見了詩人的心,感覺到了他跳動的脈搏。
在表現(xiàn)這些內(nèi)容的時候,詩人沒有直說,而是含蓄地表現(xiàn)出來,為了詩意的含蓄,詩人采用了三種手法。一種是借景抒情,借景達意,字面上是寫景,字里行間卻藏著詩人的寓意,“言在此而意在彼”。“鼓棹路崎曲,指景限西隅”。從字面看,這不過是詩人在嘆“行路難”,在埋怨日落黃昏夜幕降臨得太早;透過字面,便不難發(fā)現(xiàn),詩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對官宦生活的厭倦情緒。他怨天恨地,沒有一點歡樂的情緒。在他的眼里,江南夏日的風(fēng)光也變得那么荒涼,那么可怕,沒有歡樂的情緒:“高莽眇無界,夏木獨扶疏”。不是風(fēng)光不美,而是詩人的情緒不佳。詩人不去贊美行役途中的風(fēng)光,正說明他想結(jié)束勞累的行役生活,想離開討厭的官場。
另一種是用雙關(guān)語達意。“江山豈不險,歸子念前涂”。字面是說行路難,征途艱險可畏,可實際是說官場多風(fēng)險,吉兇難料。當(dāng)時,東晉王朝岌岌可危,孫恩在浙江領(lǐng)導(dǎo)的農(nóng)民起義軍逐漸逼近京師,陶淵明的上司桓玄屢次上表要求討伐孫恩。王室腐敗,義軍攘起,軍閥桓玄又野心勃勃,社會極具動亂,想到這些詩人不能不瞻“念前涂”。由此看來,詩人筆下的“江山”,決不僅指自然界的山川,而是指國家社稷,“前涂”也不僅僅是指征途,而且是指詩人自己在社會動亂時的仕宦前途。“江山”和“前涂”都是一語雙關(guān),值得玩味。
除了上兩種,詩人還使用了隱喻的手法。“凱風(fēng)負(fù)我心,戢枻守窮湖”,這兩句是說風(fēng)不從人愿,阻延歸期。其實,詩人的命意遠不止于此,他一連用了三個隱喻,來描述自己懷才不遇的處境。“凱風(fēng)”是可恨的,它與詩人的心相違;凱風(fēng)在這里暗指壓制陶淵明的世族權(quán)貴。“戢枻”是可嘆的,因為“枻”的作用在于劃船,當(dāng)“枻”被“戢”起來以后,就失去作用了。“窮湖”是荒涼的地方,船泊窮湖是無可奈何的事情。作者陶淵明是有才干的,然而,他只能在桓玄手下當(dāng)幕僚,而且還要行役千里,致使自己無所作為。桓玄的慕府就如同“窮湖”,陶淵明發(fā)出“戢枻守窮湖”的嘆息是很自然的,并非無病呻吟。
最后,詩人慨嘆只有百里之遠,因風(fēng)受阻,不能及早返回舊居,發(fā)出了“將焉如”的嘆息,但只不過是空嘆而已,與前面的“歸子念前涂”一句聯(lián)系起來看,這幾句詩真實地抒寫了詩人“出仕”與“歸隱”的矛盾痛苦心情。
從全詩看,首尾兩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說的方法,感情真摯熱烈。詩的中間部份則采用借景達意、一語雙關(guān)和隱喻的方法,表現(xiàn)出詩人的隱衷,富有意趣。
陶淵明
陶淵明(約365年—427年),字元亮,(又一說名潛,字淵明)號五柳先生,私謚“靖節(jié)”,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、文學(xué)家、辭賦家、散文家。漢族,東晉潯陽柴桑人(今江西九江)。曾做過幾年小官,后辭官回家,從此隱居,田園生活是陶淵明詩的主要題材,相關(guān)作品有《飲酒》、《歸園田居》、《桃花源記》、《五柳先生傳》、《歸去來兮辭》等。 ...
陶淵明。 陶淵明(約365年—427年),字元亮,(又一說名潛,字淵明)號五柳先生,私謚“靖節(jié)”,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、文學(xué)家、辭賦家、散文家。漢族,東晉潯陽柴桑人(今江西九江)。曾做過幾年小官,后辭官回家,從此隱居,田園生活是陶淵明詩的主要題材,相關(guān)作品有《飲酒》、《歸園田居》、《桃花源記》、《五柳先生傳》、《歸去來兮辭》等。
猜你喜歡
陰晦中忽見華山。金朝。馮璧。 吏部能開衡岳云,坡仙曾借海宮春。蓮峰清曉忽自獻,二公何人予何人。
張丞見和次韻答之。宋代。陳造。 我本山林人,娛老有日用。時須禽一戲,暇乃笛三弄。言償作縣責(zé),顧敢寶所重。催科未妨拙,防速牙角訟。
初至襄陽與熊心開總理夜話。。梁朝鐘。 虎帳銅壺夜氣清,羽林十萬靜無聲。單于冬入殘三輔,漢上秋成縶九營。勿慮衛(wèi)青終失寵,無勞賈詡更談兵。吳山楚水年馀別,殘角空階盡月明。
山居二十詠 其十三 雙魚。宋代。洪適。 犀角透魚龍,石肌蘊星斗。亦有無情花,枝頭魚貫柳。
華陰二蓮歌 其四。清代。屈大均。 萬仞蓮花掛碧天,飛來蒼翠玉樓前。美人雙倚仙人掌,舞袖回風(fēng)絕可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