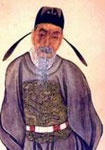調(diào)笑令·胡馬
調(diào)笑令·胡馬朗讀胡馬,胡馬,遠放燕支山下。跑沙跑雪獨嘶,東望西望路迷。迷路,迷路,邊草無窮日暮。
調(diào)笑令·胡馬。唐代。韋應物。 胡馬,胡馬,遠放燕支山下。跑沙跑雪獨嘶,東望西望路迷。迷路,迷路,邊草無窮日暮。
譯文
有一匹胡馬,被遠放在燕支山下。它在沙地上、雪地上來回地用蹄子刨,獨自嘶鳴著,它停下來東張張,西望望,發(fā)現(xiàn)自己迷路了。而此刻,遼闊的大草原茫茫無邊,天色將晚。
注釋
胡:古代對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稱。
燕支山:在今甘肅省張掖市山丹縣境內(nèi)。
跑:同“刨”。
嘶:馬叫聲。
這首小令運用象征的手法,表現(xiàn)離鄉(xiāng)遠戍的士卒的孤獨和惆悵。作者以清晰的線條,單純的色調(diào),描繪了邊地遼闊的草原風光,和徬徨在這奇異雄壯的大自然中的胡馬的形象。語言淺直而意蘊深曲。燕支山,即焉支山,位于甘肅省永昌縣西,古長城附近。唐代此地與東突厥接壤,是邊境。這是此詞所涉及的地理環(huán)境。從詞中首先可看到燕支山下的四季風光。春,風沙撲面;冬,大雪蓋地;夏,綠草如茵;秋,天高云淡。胡馬就活動在這樣的背景中。作者描寫了一天中馬的生活,它是在與風雪搏斗和期望中度過的。詞的末句攝下的是,在桔黃的渾圓的落日漸漸沉沒到地平線下,暮藹籠罩大地那最易引起鄉(xiāng)思離愁的時刻,胡馬在天邊的草原上的孤寂形象。仿佛它在為歲月有限與草原無限的對比而悵惘。在對景物的描寫中處處交織著胡馬的情緒。
詞作寫了邊地風光而并非主旨。在對馬的擬人化的描寫中,揭示了它的象征意義。“遠放燕支山下”,“放”字已說明胡馬非野馬。“放”前著一“遠”字,令人遐想。“遠放”既給人以遼遠的空間感,又使人見出“胡馬”并非胡地之馬,而是被遠遠地放到接近胡地的馬。這時已使人感到馬的象征性。但從進一步的描寫中,象征意義就明顯得不容置疑了。一般說來,放馬時間是在夏天水草肥美,沒有戰(zhàn)事或農(nóng)閑的時候,目的是節(jié)省草料,并使馬吃到鮮草而肥壯。而“跑沙跑雪獨嘶,東望西望路迷”,又寫這匹馬在風沙中、在大雪中迷失道路,不停地奔波,孤獨地嘶鳴,惶惑不安地四處張望,尋找著、呼喚著伴侶。仔細揣摩,就會發(fā)現(xiàn)其中有兩點矛盾:一,“放”馬不會在風雪中;二,既然“放”馬,馬必有主人,不會迷路。產(chǎn)生這些矛盾不能歸結于藝術高于生活,是因為作者把馬當作人來寫。如果將馬看作是戍卒的象征,就合情合理了。“迷路”是戍卒的感覺,與“何處是歸程?長亭更短亭”意近,而春秋代序,年復一年,在塞外無邊風沙中長期戍守正是戍邊戰(zhàn)士的生活。
此詞用準確精煉的詞語,含蓄曲折地表現(xiàn)了馬的情緒,即戍邊戰(zhàn)士的情思。“遠放”、“獨嘶”、“無窮”這三個詞都有一定的相對性,遠對近,獨對偶,無窮對有盡。正是這種相對性的張力表現(xiàn)了戍卒在此種情境中對彼種情境的向往。即戍卒從內(nèi)地被遣放到邊疆的感受、征戍生活的艱苦和思親盼歸的心緒。輕松的筆調(diào)表現(xiàn)深刻的主題,平淺的語言有著豐富的內(nèi)涵,淡筆勾勒的畫面浸潤著濃郁的感情。
韋應物
韋應物(737~792),中國唐代詩人。漢族,長安(今陜西西安)人。今傳有10卷本《韋江州集》、兩卷本《韋蘇州詩集》、10卷本《韋蘇州集》。散文僅存一篇。因出任過蘇州刺史,世稱“韋蘇州”。詩風恬淡高遠,以善于寫景和描寫隱逸生活著稱。 ...
韋應物。 韋應物(737~792),中國唐代詩人。漢族,長安(今陜西西安)人。今傳有10卷本《韋江州集》、兩卷本《韋蘇州詩集》、10卷本《韋蘇州集》。散文僅存一篇。因出任過蘇州刺史,世稱“韋蘇州”。詩風恬淡高遠,以善于寫景和描寫隱逸生活著稱。
猜你喜歡
送少參歸安韓公兵備廣右兼懷方伯喬公督學劉公。明代。葉春及。 昔余寄薄游,并公宰閩邑。翩翩丹山禽,千仞亦棲棘。拙劣守故丘,公獨崇明德。建節(jié)炎海隅,晤言慰疇昔。昨來祗簡書,忽有西甌役。漓江豈不遙,旬宣美臣職。胡由事攀留,壺漿望如渴。矯矯云間公,夢寐猶顏色。劉君鄱陽彥,賤子實親識。嶺樹搖心旌,一別云泥隔。行矣各致辭,努力加餐食。
贈張濆榜頭被駁落。唐代。趙嘏。 莫向花前泣酒杯,謫仙依舊是仙才。猶堪與世為祥瑞,曾到蓬山頂上來。
酬李寄軒。。釋智愚。 寄傲知何所,行藏匪一軒。究心無別旨,鳴道有來源。未先通理不,聲詩不在言。相期湖上寺,執(zhí)手聽啼猿。
哭稚女雁 其一。清代。屈大均。 當年設帨雁門關,代北諸軍盡解顏。共道榆林飛將種,明駝莫載木蘭還。
白皦春辭。明代。胡汝嘉。 小窗西畔月輪斜,銅博山前散紫霞。宴罷不知春夜促,醉憑紅袖看梅花。